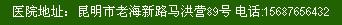|
心系山区北京中科医院温情相伴 https://myyk.familydoctor.com.cn/2831/content_920754.html一九八五年秋天,我正式入读宁夏青铜峡市邵刚乡二旗村小学。在此之前,我曾在邻村的五道渠小学读过一年学前班,班主任是汤晓虹老师。学前班报道那天很有意思,是我爸安排我三叔去送我。三叔拉着我的手,走到半路,遇到了十七岁的汤晓虹老师。晓红老师和我爷爷家住一个队,图省事的三叔见状,直接把我交给晓虹老师。他问晓虹老师学前班学费是多少,老师说5角,是的,没听错,一学期是5角钱!我三叔当即就掏了5角钱,递给老师。老师拉着我的手去了学校。我在五道渠小学度过一年非常美好的时光。乡下没有幼儿园,只有学前班,俗称“半年级”。有的孩子会选择上学前班,有的孩子可以直接上一年级,这个没硬性规定,主要看年龄。甚至有些学习特别出众的孩子,还可以跳级。之所以选择在五道渠小学上学前班,主要是当时的二旗村小学位于大西边的唐徕渠畔,距离我们最东边的五队比较远。五道渠小学距离我祖父和外祖母家都比较近,能够寄宿。等我要上一年级时,二旗小学正式迁址到距离各小队距离适中的地方,离我们队的距离比先前近了一半,不用再寄宿在祖父家和外婆家,理所当然转了过来。一年级开学前一天,我跟着一帮孩子去了一趟二旗小学的老校区。老校区位置比较偏远,位置在现今的二旗村四队南侧,东侧紧挨着一条土路,土路的另一侧是一望无垠的玉米地,一派田园风光。学校附近有一座庙,规模似乎还不小。学校西边,步行不远就是唐徕渠,渠边绿树成荫,风景旖旎。漫步老校,不多的两三排校舍安安安静静坐落在那里,学校围墙边有几棵高大参天的沙枣树,起风的时候,能听到树叶沙沙作响。听说,每逢金秋十月,会从头顶扑通扑通落下金黄成熟的沙枣,想想就令人心驰神往。老校区我只去过一次,短暂的停留,在印象里却永久地定了格。开学报道后,我们正式转入了新校区。我姐比我大一岁,和我同时在五道渠小学上完学前班,又同时转学到二旗小学。我们那一届学生多,分了两个班,我姐在1班,班主任是张廷环老师,我分在2班,班主任是黄凤霞老师。两位老师都是本地人,家都在二旗村三队。小学老师几乎都是本地人,其中又有一半是本村人。搬迁后的二旗小学位置突出,它位于邵刚乡东西主干道与南北主干道交汇处东北侧。学校坐北朝南,四四方方,校门开在南边围墙偏东的位置。出了大门是一条一米多宽的东西向灌溉水渠。水渠上有座石板桥,春、夏两季渠水潺潺,是我们放学戏水游玩的好地方。水渠南侧的宽阔马路,往东可以直达邵刚乡政府驻地(现在的兴邵街),往西穿过二旗二队的村道可以抵达唐徕渠边;西侧围墙外的马路,往南可以通往五道渠、东方红、营桥等村,往北可以去往永宁县的西邵、宁化、黄羊滩农场等地(现在的石玉路)。北侧和东侧都是农田。四边围墙下都有水渠,每年春天我们都会去围墙下种树,年年种,似乎年年成活率都不高。校门口一年四季都有卖零食和各种小玩意的。春天有卖枣子和柿饼子的。那枣的个头比我们当地出产的沙枣要大,但是比我们现在吃的那种大枣又小很多。花一毛钱能买一盅,那盅的个头也就小茶杯那么大。买上一盅,装进兜里,慢慢品尝。不得不说那枣的味道真好,不酸不涩,软糯香甜。卖零食的小贩是个六十岁的的老太太,好像是隔壁五道渠村的。她每天都会在校门口忠实地守候。卖起东西,眼疾手快,锱铢必争,该给多少就给多少,从不多给。有调皮的孩子多拿她一两个枣,她保准飞快地抢回来。在我们乡下,但凡能做点小买卖的,都是颇有头脑的人,他们大多精于人情世故,是乡下人眼里的能人,也是异类。对这类人,普通大众羡慕妒忌,同时也会抱着某种偏见,认为但凡做买卖的,都善于算计。得时刻提防。本质上,这里属于乡土社会,时代务农,乡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夏天,最多的就是卖冰棍的,有时候有好几个扶着自行车的小贩在那竞争。五分钱的冰棍,一毛钱的奶油雪糕,倘若口袋里再阔绰,还有两毛钱的大冰砖可供选择。汽水都是袋装的,液体通红,配了色素。记得有一种两毛钱的汽水,外包装是葫芦状的透明塑料,喝的时候,得转着圈,用牙把“葫芦口”咬开,喝完了还可以当玩具玩。秋天的时候,可卖的东西就多了,小苹果、小果子之类,论个卖,把小孩们馋的呀!还有一种卖圆球状米花糖的,小贩很有头脑,它会使用一个转盘,盘面上分成很多刻度,里面画着一个到十个不等的圆点。转盘前面有个扳机,里面放着飞针,引诱小孩花两毛钱,一只手猛转一下转盘,另一只手扣动扳机,飞针射到转盘上,射到的圆点有几个,则可以换取到几个米花糖。元旦前夕,卖贺年片和印刷画的就特别多。贺年片两毛钱一张,同学之间买了互赠。能收到多少张贺年片,则证明了这个人的人缘和班级地位。毕竟是乡下,不富裕的人多,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来买这些玩意。但是,和农村礼尚往来的陋习一脉相承,倘若别人赠给你了贺年片,你不回赠,会让人轻视,甚至是遭受闲言碎语。没钱,那该怎么办呢?只能用橡皮或者小刀把别人赠给自己的贺卡背面的赠言擦掉或轻轻划掉,再写上新的赠言,转赠给别人。拆东墙补西墙,如此反复,很像现实世界中的大人,互相倒腾着送礼。涂改后的贺卡旧迹能看出来,收到的同学肯定不太高兴,但是总比不回赠要强太多。当时的贺卡,正面大多是当年流行影视剧的人物剧照和各种旅游景点风景照,威风凛凛的美猴王和贾宝玉和林黛玉凑在一起读书的那种卡片最受我们欢迎。还有那种卖油画的,一尺见方,很薄,两毛钱一张,不用固定,直接就能贴在家里的水泥墙上作装饰用。记得五年级时,我有一次花了四毛钱买了两张油画。画太薄,小贩数的时候没拈开,实际上是三张,我没有声张。回家后还向我爸炫耀这事,记得当时我爸说了一句:“小时候偷针,长大了偷心”。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多拿过别人任何东西,父亲的这句话到今天我还深深记着。学校四周都是高大的围墙,西南角四四方方的一块,属于二期村村部。村部北侧是一排办公用房,除了村里开会,常年不见人影。偶尔有上面下来挂职蹲点的干部,基本都被安排在了这里居住。村部东边挨着学校的围墙上曾开过一个小门。我们常常跑去村部里面瞎转悠,小孩啥都好奇,时不时踮起角,趴着窗户往那几间办公室里乱瞅,总期待着发现点什么。记得有一个下雨天,我一个人课间又溜到村部的院子里去玩,鬼使神差,又想趴着窗沿往里面瞅,手刚碰到窗户上的钢筋,一股电流一下就穿越了我的身体,我被“送”出了两米多,狠狠地摔在地上。爬起来我才发现,屋檐下的电线接头破损了,流过裸露接头的雨水又流到了窗户防盗的钢筋上,我刚刚触电了!试想一下,如果我当时不是用手去碰,而是直接去抓那根钢筋,后果不堪设想。那时候的农村,用电没什么安全性可言,经常听说有人被电死的,不像现在有漏电保护器和三相五线制,安全措施很齐备。总之,从那以后,我害怕了,再也不敢走进那排办公用房,尤其是下雨天,更是躲得远远的。村部西侧是几间南北罗列的库房,里面停放着村里最重要的固定资产:大型拖拉机、耕犁、圆盘耙。每年春秋,都是这些”大家伙”大显身手的时候,整个大地都归他们掌控。驾驶庞然大物的拖拉机手,更是我们小孩眼里的英雄。库房西北角挨着学校的是一堵围墙,围墙上有个土蜂窝,数不清的土蜂无时无刻不在飞进飞出。土蜂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毒虫,个头比普通蜜蜂大上一倍,异常凶猛,倘若被叮,简直是灾难性的后果。土蜂一般不怎么主动叮人,除非主动攻击它们。但一些孩子就喜欢玩刺激,胆大的孩子会拿着石头或者土坷垃,悄悄溜到土蜂窝前,瞄准,发射,对着土蜂窝迅速发动攻击,然后转身快跑。受到挑衅的土蜂立刻出动大股部队,数不清的土蜂四面出击,铺天盖地,对着“捣蛋鬼”们穷追不舍。跑的慢的就很可能被咬,不过被咬到的情况似乎不多。乡下孩子之所以跑的快,身体好,就是和土蜂、恶犬们比赛练就的。学校南围墙外,从西往东,是一溜门面房,大概有七八间。有理发店,粮油店,农机修理部,不过经营业务经常换。二旗村这个地方,人口不多,距离乡政府驻地距离也不远,很难形成商业氛围。放眼整个邵刚乡,除了玉泉村,其它村办商业都很惨淡。如果一定要找出生意比较好的门店,也不是没有,譬如最西头的“鑫鑫商店”,占据金角银边,财源滚滚。商店门口有卖肉的,肉贩是五道渠人,一对父子,大概姓宋,父子俩身体都很精壮。西头挨着商店的一间房,里面曾有个鞋匠,姓刘,手艺很精湛。门脸房中间的几间,先后开过裁缝店和理发店,还有一间农机修理部,生意还不错。门脸房的最东头的一间,在-年,曾一度是我父亲开过的诊所。那个时候,我已经从二旗小学毕业,就读邵刚中学。我父亲人生最辉煌的一段岁月大概就是折腾起了这么个小诊所。它也是我们一家人的希望和寄托。我父亲年轻时曾是青铜峡知名中医——医院院长鲁XX的弟子,医术还不错。年轻时,父亲曾作为赤脚医生,跟着师傅活跃在乡村医疗一线,后来结婚后专事务农。没想到四十多岁时,又赶上了乡村医疗事业蓬勃发展的风口,父亲重操起旧业。只有我们知道,务农的那些年里,父亲手不释卷,家里成堆的医学书他翻了一遍又一遍,专业从没撂下。但是,就是这个小小的诊所,在我上高中后,被上级管理机关取缔了,说是违法经营,被没收走了很多器械和药品。父亲不甘,又转战到了临近的五道渠村,刚刚有点起色,又被取缔了,父亲屡败屡战,零零散散坚持了五六年,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在我上高中那几年,总是拿着父亲反映情况的上访信在县城的各个角落里四处找人托关系。不停奔波,吃了太多闭门羹,遍尝冷眼。父亲的失败,很大原因就是我们家上面“没人”。很多人的医术不如我父亲,有的连执业证照没有,还是能正大光明地经营,轮到我父亲,就是不行。后来父亲被迫“撤摊”,我们爷俩在月黑风高的夜里,由我开着小四轮,把诊所里的东西往家拉。父亲坐在旁边,一路给我陈述人生受到的各种屈辱。直到几十年后,每当回首往事,当他感受到不公的时候,就会不厌其烦讲上很长一段,讲着讲着他就会哭。要知道,在外人眼里,他曾经是多么狂傲的一个人啊,放在古代,估计我都得跪着听才能慰藉他那受伤的心。二旗小学校园内的前半部分,挨着村部的东边是两排东西分列的教室,一共有八个班级。中间是一排办公室,后半部分的东侧一小块是几间简陋的旱厕。西侧是很大的一片校田。教室和办公室都是红砖、平顶、还有透明的玻璃窗,这在当时已经是乡下很阔绰的建筑了。教室里配备的都是新桌新椅,我们赶上了头一拨,非常幸运。教室里都是用灰砖铺地,西面墙是黑板,黑板的面积很大,讲台也高出地面很多。课桌都是大桌子,并排能坐三个人,椅子是长条凳。如果三个人一起坐,中间和一侧靠边的人突然站起来,长凳保准会翘起来,另一侧的人反应不灵敏,保准栽倒在地。课桌上往往会被小刀刻意画出一条条直线,那是男女的分界线。因为越界,男生女生扭在一起厮打是常事,不过过一会又和好了,小孩子家家,还太不懂羞涩和矜持。粉笔和板擦都是学校统一购置的办公用品,只有教鞭是学生用木棍削成的。钢笔粗细,长约一尺。要求笔直,一般是用杨树枝削磨加工而成。老师没事就拿着教鞭敲黑板或者敲学生的脑袋。杨木材质比较脆,很容易折,所以,教鞭的需求量很大。也就奇怪,班里总有几个心灵手巧又很能讨好老师的同学,他们永远都不会让讲桌上的教鞭短缺,并且他们做出来的教鞭粉白溜光,粗细适当,是老师眼里特别趁手的“兵器”。教室东墙上也有一块黑板,用来办黑板报。不过我们都是小孩子,除了个别聪慧富有创作天赋、心灵手巧、能写会画的同学,大多数人都很笨,所以出黑板板的任务就由班主任老师负责了。勤快的班主任老师两个月更换一次黑板报内容,有的一年都不愿意更换一次——除非上级检查。教室冬天采暖主要依赖土炉子。每年十一过后,学校会弄来一大卡车煤,每个班级会分到一堆。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自己用模具“拓”煤饼,晾干后搬进教室,堆在最后边的角落里,用来烧火取暖。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到了冬天正式取暖,每年大清早,当日的值日生都要早早到校生炉子,晚上还要封炉子。如果煤质不好,室内通风条件又不好,全班同学上着课就感觉头晕脑胀,不用问,一准是煤气中毒。我们管这叫“被煤气打了”。如果当天值日生发现昨晚炉子没封好,火死了!没办法,只能重新再生。一时间,教室里黑烟滚滚,呛得人咳嗽连天,眼泪往下掉。再看那趴在炉子边扇风的同学,脸上黑呼呼一片,跟刚从煤窑里爬出来一样。课间的时候,有的同学会拿出家里带的小苹果,放在炉盖上烤。我有幸尝过,味道好的不得了,如果带的是地瓜,好家伙,上课时整个教室都弥漫着一股香气,人人都掉哈喇子。每个班级教室前面都有一小块两平方左右的花圃,四周用十公分高的砖头围成一圈。春天的时候,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撒下花籽,盖上薄膜,一个月后,在薄膜上掏个小洞,就能看到绿油油的嫩芽。再过些日子,撤去薄膜,满眼嫩绿。地雷花、牵牛花、月季花等等各样的花儿猛吮雨露,撒欢了一样疯长。在我们乡下,自己种殖的鲜花不多见,我们都把这个小小花圃当做宝贝一样看待。我们不惜从自家里偷来化肥悄悄撒进去,还会不时和别的班进行比较,看哪个班的先开花,哪个班的花开得最多、最艳。校园中间的一排办公室,东头两间住着我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封彦礼老师一家。封老师是唯一家住学校的老师。中间两间属于校长,一间办公,一间做宿舍。每天放学以后,当所有人都走了,夜深人静,校园里黑乎乎一片,只有封老师家两间房子灯是亮着的。办公室最西头有个高大的水泥杆,上面安着四个大喇叭,分别冲着二旗一队、二旗二队、二旗三四队、二旗五队几个方向——这可是我们村的“通讯生命线”。有时候我们上着课,就听到村书记在校长室用大喇叭广播:“各队党员开会了,各队党员开会了,各队党员开会了”,有时候能一连重复好多遍。要么就是“挖沟了,走了,挖沟了,走了,挖沟了,走了”。当然,唯一令孩子们兴奋的是“今天晚上二旗X队有电影,二旗X队有电影,电影的名字是XXXXXX”。大喇叭声音辽阔,能传很远,没有电话的年代,它就是王者!教舍西侧,也就是挨着村部北侧的一块是运动场,面积能装得下两个篮球场。我们平时上体育课都在这里,体育课就是跑步,做操,然后老师给个足球篮球,自己玩。再往北是学校里的公田,一直到北侧围墙边,面积足有四五亩。一年水稻一年小麦轮着种。如果是种小麦,就会套种玉米和甜菜之类。这些田基本都是由高年级学生负责打理,插秧,掰玉米,挖甜菜,打场,这些活我上三年级以后都陆续参与过。不过,究竟最后的收成都去了哪,我们不知道,也不敢问。可能是公田的缘故,学校也不怎么上心,毕竟很多活是我们小学生干不了的,譬如背着喷药器打药之类,也不能指派男老师去干。暑假里没人,稻田全是杂草,总不能把学生都招呼回来下田薅草吧。种种的种种,只能导向一个结果,那就是校田每年的收成似乎都很差。封老师住校,挨着他家后面的地方,专属的一小块是他的菜地。他会种些蔬菜,辣椒、西红柿、豆角之类的平常食用。蔬菜长势不是那么太喜人,不过该收获时节就能有收获。封老师是年生人,他做我的班主任时已经50多岁了,中年丧妻,一个人养着三个孩子,靠教书维持生活。他是生活的强者,好像也是我们二旗小学当时除校长以外唯一的事业编制,工资应该也很高。封老师在当地很受人尊敬,关于他的故事,我在《我的恩师封彦礼老师》一文中已经写过,这里就不再赘述。描述了很多校园的外围,是到该说说那些熟悉的老师和学生了,否则这篇文字永远结不了尾。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小学校长徐生成,四十出头,不苟言笑,穿的很体面,其人颇有一些治校手段。他有个儿子也在我们小学就读,和我姐同班。每天很早,他都会从很远的星火村骑车带儿子到校。放学父子俩一起回去。有时候儿子调皮捣蛋,或者违反纪律,徐校长知道了,也不维护,上去连踢带踹,宝贝儿子吱哇乱叫,他不管不顾,毫不留情。徐校长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记忆有两次。一次是我们村有个“社会青年”,姓名我忘了,没事就带着一伙人上我们小学溜达。有一次社会青年可能觉得太闲了,为了炫耀一下自己的身份,他跑到我们学校的操场上,跳起来用两只手交换着一节一节往上拔篮球架的斜拉杆,他也确有蛮力,一直攀拔到了最高点。这个时候,悲催了!用来压篮球底座的石板没有经受得住重量,当时就翻了,篮球架轰然倒地,辛亏这个“社会人”躲得快,否则一定会被砸到。徐校长闻讯赶来,毫无畏惧,直接指着这个“社会青年”劈头盖脸一顿数落。“社会青年”一幅牛哄哄的样子,还想扑过去怎么着,丝毫不把校长放在眼里。徐校长狠狠甩下一句:“信不信,我找你二妈去!”三十多年后,我依然很清晰地记得这句话,徐校长“祭”出了对方的“二妈”,看来这个“二妈”大有来头,大概是乡政府干部之类吧。反正,这话一说,社会青年的气焰立刻就被打消了。那个年代。农村乡下总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青年,不事生产,扰民滋事,寻衅欺小。这些人之所以肆无忌惮,都是有着一两个所谓“靠山”,放在今天就是“官二代”。拉虎皮做大旗,上面有个芝麻大做官的亲戚,就立刻高人一等。其实他们那些拙劣的表演,二妈、三爸们未必知道,但是农村人都比较怕“官”,就见了大队书记都得立刻矮三分。对徐校长的记忆,还有一次是年,我当时上高三,所就读的青铜峡一中学生宿舍改造,寄宿生没有地方住,要到外面自己租房子住。我和弟弟在城郊的小坝乡小学里找房子,偶遇当时已经调任到小坝乡中心小学担任校长的徐生成校长。只可惜我和弟弟记得他,他不记得我们。我们和他讲了想从这所小学里租间空房,也讲了我们曾是二旗小学的学生。听完以后,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很果断地拒绝了。其实当时有很多同学都在那所小学租下了空房。作为校长,可能他带过的学生太多了,也可能他一直都是那么地不徇私情。在二旗小学,除了封彦礼老师外,记忆较深的是张廷环老师,教语文。他是我姐姐班的班主任。张老师和我父亲差不多年龄,声音尖亮,为人热情干练,行走如风,富有生活激情,对教学工作很认真。张老师家里孩子多,好像生了很多姑娘,总见他忙忙碌碌,总在辛苦奔波。赶上农忙时节,他不是在田间地头育苗,就是在三尺讲台上育人。他一生从未脱离过教学事业,后来似乎做了主任,也算功成名就了。正应了那句话:伟大是熬出来的!我一年级到四年级的班主任,是黄凤霞老师。黄老师三十岁出头,个子不高,很严厉,身材中等,微胖,虽然是女性,但是“修理”起学生来,稳、准、狠、快,手段丝毫不逊男老师。小学老师惩罚学生的方式最轻的的是罚站,站在座位上,站在讲台下面,站在教室外面等等。此外就是扇耳光、踢屁股,除此之外。他们各个都是投掷高手,粉笔头、黑板擦,无论学生离着多远,一砸一个准。但是,这些都是我们黄老师练剩下的,她是伟大的发明家,创新动作层出不穷。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当时我们班有个姓刘的同学,是二旗二队的,平时喜欢调皮捣蛋。有一次自习课大声说话,被黄老师给逮着了。黄老师二话不说,让他站到讲桌上,让另外四个也交头接耳的学生一人捉住桌子的一个角,使劲摇桌子,谁不用力摇就立刻给谁一教鞭。谁都不敢糊弄,四个人使劲摇。站在上面的刘同学身体左摇右摆,吓得面如死灰,不断哭丧告饶。诸如此类惩罚手段的发明成果,黄老师还有很多,完全可以申请专利。我上三年级时,有一次黄老师批改数学作业,我有几道错题。当天黄老师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事,心情不好的缘故,把我叫上讲台,指出错题给我看,然后二话不说,对我使劲推了一把。我没有丝毫准备,踉跄着被推下讲台,脑袋当即磕到窗台上一块横放的玻璃角上,脑袋就被划了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黄老师一看,出事了,连忙丢下一切,带我到附近的小诊所治疗。当时也没有麻药,医生直接拿着鱼钩状的针,划拉我的头皮,一连缝了好几针。我竟然没觉得疼,可能流血流的麻木了。黄老师骑着自行车,把我驮在前面的大梁上,送我回家。到我家后,我妈正在院子里搓草绳,黄老师对我妈说是我自己不小心磕破了头,她带我去缝了几针,直接把我送回来了。我妈当时就明白了,也没说话。黄老师说完就急急匆匆走了。后来我爸回来了,知道了前因后果,说算了吧,论起来,和黄老师连带着也是亲戚,这事就算过去了。黄老师家农活特别多,我们上二年级,还是不到十岁的孩子,就被要求去给她家干各种农活。她从来不安排自己队的孩子,或者是那些村干部,或者有头有脸人家的孩子给自己干活。黄老师后来和丈夫离异了,在我们升五年级时离开了教师岗位,我们也终于算是解脱了。黄老师也有对我们好的时候,譬如有时候,下午她给我们上课,当她感觉自己太累了,就会让我们集体趴在桌子上睡上一节课,她也会趴在讲桌上陪着我们一起睡,有一次一直睡到放学。冬天,班里咳嗽的学生特别多,黄老师会想办法弄来桔子皮,熬成一锅水,我们一个个排着队,一人喝上一碗。其实,自始至终,我对黄老师都没有太大偏见。反而,我认为她是个值得称赞的女强人。记得年,那是她离开教育行业四五年后。我在集市上遇到了她,她在那摆摊卖水果,动作麻溜干练,看见我还很热情地聊了会。她和她的家庭,在当地曾流传着很多的传说。农村女人一旦好强,就会有各种故事。但是,我个人觉得,在黄老师本人看来,一切都是浮云。此外,还有熟悉的贾传勇老师和胡金萍老师。贾老师是我五六年级的数学老师,我们也是一个队的邻居,后来两家还成了对门。贾老师对我们也很严厉,他也喜欢惩罚学生,可能小学老师中,就没有不打学生的——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不听话。小学时代的老师基本都是初中学历,高中毕业的都很少,教师素质可想而知。他们入不了体制,教一天是一天。严格意义上只是临时工,一手执着教鞭,一手扶铁锹,管教学生除了简单粗暴,还是简单粗暴。我上五年级时,中秋前夕,我们村承包最南头果园的那户人家,通过贾老师找我们学生去帮着摘苹果。我们听说后都非常兴奋,谁都清楚,去了可以随便吃。这个时候,我们班的张铁梅同学站了起来,说他家要找几个同学去干农活(削甜菜皮),贾老师想了一会,点了四五个人,这里面就有我。说实话,我很气馁,但是没办法,张铁梅的爸爸是村会计,贾老师肯定要唯命是从,我是班里最没有家庭背景的,我不去谁去。那天,去给张铁梅家干了一天活,晚上我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恰好遇到贾老师,他的自行车后座上驮着满满一袋子苹果,不用问就知道是果园给他的“报酬”。贾老师看到我,有点意外,可能也觉得过意不去。他跳下车,从袋子里掏出了几个苹果硬塞给我,但是我没要。还有一件小事,是学校六一儿童节要参加乡里的体操比赛,我被体操队选中了,但是我没有学校要求的那种服装。我妈带着我上贾老师家去说情,让我退出体操队,他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最后没办法,我妈只能狠下心,卖了粮食,给我买了服装。无论黄老师,还是贾老师,还是我生命中遇到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个底层的人,但是倘若他们拥有了一丁点权利,就会把这点权利发挥到最大。这是人的本性。胡金萍老师,是我们小学出名的一枝花。我没记错的话,家是高渠的,父亲好像是高渠村的大队书记之类。胡老师为人热情爽朗,到我们小学教书,再后来就嫁给了贾老师。风风雨雨,不畏世俗,夫唱妇随,两个人也走过很艰难的路。记得我们五年级的时候,春天,贾老师带着我们去春游,我们高年级的同学走在前面,低年级的学生走在后面。我们踩着水面上的石头,一路越过刚刚解冻的唐徕渠,掠过果园和高高的西干渠堤坝,一路向西。最后进入一片戈壁沙漠,抵达一处高大的烽火台下,我们管它的名字叫“二旗堆”,这个烽火台很显眼,在村子里向西眺望,哪个角度都能看到它。以二旗村命名,它存在的年头可能有五百年,也可能有上千年,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古老苍浑,一直默默地矗立,守候着这方土地。我们登上高高的“二旗堆”,挥舞红旗,颇有凌云壮志雄心。我们从来没有步行过这么远,也没有想过我们的村庄距离沙漠戈壁这样近。夕阳西下,站在烽火台上举目东眺,远处是一望无垠的庄稼地和一个又一个挨挨挤挤的炊烟袅袅的村庄。转身瞅西,在一脉枯黄的沙漠戈壁中,一列绿皮火车从巍峨的贺兰山下从北向南飞驰而过........那是我们小学时代的唯一一次春游,对我一生影响都很大,开阔了我的人生视野,为此,特别感谢贾老师。我最后一次见贾老师大概是十五年前,我最小的弟弟在乡下农村结婚,主持婚礼的就是贾老师。那天也见到了胡金萍老师,他们两口子还是那么年轻,还是那么郎才女貌。那个时候,听说他们已经不教书了,自己做起了生意。相信凭借他们的知识和阅历,必定能成为当地人中的佼佼者。还有一位二旗一队的女老师,姓何,爱美,喜欢打扮,曾教过我们数学,对我不错。还有很多很多老师,有着太多的记忆,三十年过去了,终归还是没能记住名字。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生活就是这样,来来往往,每个人都是别人的过客。小学阶段,当然最隆重的日子是六一儿童节,乡里一年一度的儿童节,都会举行全乡小学的比赛。我们二旗小学的霸王鞭表演和体操表演出类拔萃,经常拿第一,贾传勇老师和胡金萍老师负责指导,对这方面他们很有一套。小学每天早晨,大概是八点左右到校,八点半上第一节课,上午三节课,十一点半放学。回家吃饭,下午两点返校,有时候是两点半,下午一般是两节课和一节自习,功课很轻松。每天,各个小队的孩子都会结伴上学。放着大路不走,大家一定专走小道。尤其是冬天,田野里总会留下一串串清晰的足迹。还有结了冰的排水沟里,高大枯萎的蒲草里往往可以藏人,走在前面的小伙伴都躲起来,等后面的人路过,猛地跳出来吓对方一跳。夏天天热,我们中午回家吃饭,返学的时候会带水,家里条件好的用军用水壶,装的都是茶水,还放了白糖。条件一般的就随随便便找个有盖没盖的白酒瓶子或者罐头瓶子灌满开水,也有带米汤的,不过天热容易馊。我们也很爱护班级,希望把它打扮的漂漂亮亮。有的同学会折几枝沙枣花插在空瓶子里,黄灿灿一片,馥郁芬芳,能香上好长时间。有的同学会从沟里渠里的淤泥里挖来茨菇花,叶子像飞机,花朵像铃铛,养在罐头瓶子里,放在窗台上,煞是好看。西北的冬天很冷,我们穿的总是不够,手脚冻麻木是常有的事。记得有一次我手麻了,解不开裤腰带(裤腰带不小心打了死结),最后是我的一位同学用铅笔刀给割断的,方才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夏天的时候,我们会用很厚的瓶子底做凹凸镜,把阳光聚焦成一个点,能烧着墨纸。冬天太冷,我们在外面的墙边挤成一团,越挤越热乎。小学阶段,我的成绩一直一般,考试还常常有不及格的情况,每次拿到成绩单(小红皮学生手册),都会偷改成绩,69改成89,58改成88,也就奇怪,每次都能骗过我爸。我们的语文课本都非常好,很多画面和课文我今天都还记着。上面的内容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是非常向往的那种生活。五六年级,我的成绩稍微有了起色。小学最后一年,我终于拿到了小学唯一的一张三好学生奖状,也算为我的学生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总之,我一直都是人群中普普通通的存在。我知道这一生自己终究归于平凡,但是内心始终不甘平凡,至少不甘于平庸,我总是有着独特的洞察力。我们班有二十多个学生,五个小队的都有,大多数人我都还记得。其中记得一队有一家何姓兄妹,哥哥脾气暴躁,是我们班出了名的”小霸王”,没人敢惹,我和他干过很多仗,每次都是我吃亏。妹妹性格温和,甜美大方,总是看不惯哥哥的所作所为。我给他们家干过几次农活,他们的父亲很和善,做得一手好饭菜,还有个弟弟,伶俐乖巧。二队上的同学最多,刘伟、张铁梅、张丽萍……剩下的一多半都姓何。现在唯一还保持联系的是何立宁。何立宁家是书香世家,他爷爷曾是校长,父亲也是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祖辈有着耕读传家的美誉。他们家有很多藏书,家里人也舍得给他买新书,我上小学时读过的书,基本都是从他那里借的,他是我一生都值得感激的人。何立宁现在也是我们那个班级,甚至是我们村,我们乡、甚至我们市最有名气的人。他是宁夏著名的书画家、雕刻家、金石家,作为宁夏作协主席张贤亮先生的得意门生,作品曾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我现今书房墙上张贴的“馨予西风”四个字还是他题赠的。(馨予是我爱人的别名,西风是我的别名)三队上同学也很多,任全华、包建华、秦学军、秦学岭等等,其中我和任全华关系最要好。全华家条件不错,是我们村很少冬天能在屋子里装土暖气取暖的。小学时我没事就上他们家找他玩,一家人都很和气。年,我去银川罗道庄找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没想到在女同学的学校偶遇了任全华,那时我们早已失去联系。恰好他在那所学校就读,看到我,二话不说,就拉着我去外面吃了一顿砂锅大餐,那顿饭丰富的程度颠覆了我想象。四队上记忆比较深的同学,有栗平、栗学芳(栗莉),冯晓艳几位。栗平是我们班长,为人厚道仗义,能说会道,责任感很强,具有很强的领导力,在班里我一般都是给他打下手。班主任封老师有什么婚丧嫁娶的应酬,一般都是安排栗平和我替代他去。栗平骑车驮着我,或者我驮着他,俩人一路优哉游哉,一路留下很多回忆。栗学芳,现在改名叫栗莉,我们不仅是小学同学,后来也是初中同学。一头短发,非常干练,很像男孩子的风格,性格外向,天不怕地不怕。她是我们班的运动健将,和男孩子打架就从没吃亏过。和我关系一直比较友好。后来初三时,我的政治书丢了,临近中考了,急得啊!她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政治书送给了我,她说,反正自己也考不上,不用温习了。那一幕到今天我都记着。直到现在,我们都保持着当年的纯真友谊。她每次回村,都会拍点庄稼地的照片发给我。她外表有多冷酷,内心就会有多火热,我们几十年不见,却心心相通,彼此都永葆着纯真赤子之心,那是对故乡独有的深情和眷恋。冯晓燕,大概是五六年级才转入我们学校我们班的,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爱笑,喜欢穿碎花裙子,写得一手秀娟小字。小学毕业那年,我曾从她那借到一本白话版的《聊斋志异》,看的很痴迷。她也不管我要。最后,当我要还她时,她执意送给我做毕业礼物。因为她长得好看,就有个别比较捣蛋的同学经常欺负她。我这个人好打个不平。这个时候我就会勇敢地站出来维护她,结果就是被对方痛打一顿。下次我依旧站出来,再被痛打一顿。上初中后,她分在5班还是6班我忘了。我们来往不多,交集越来越少。但是,这么多年来,在我心目中,她始终都是巧目倩兮,温柔似水的可爱模样。我们五队同班的共有五个同学,分别是鲁生明、我、常海萍、陈红霞、刘慧玲。两男三女,我们经常结伴上学、放学,关系亲密,非常团结。和每个人的交往,都有很特别的记忆和故事。六年级毕业时,我和鲁生明两个人曾跪在一颗大柳树下发誓:以后无论谁考上大学,都不能忘记对方。十二三岁的我们,该有多单纯。可能那时候我们觉得上了大学就可以出人头地,能当大官,能改变一切。后来我们都升入了邵刚中学,我和常海萍有幸分到了1班,刘慧玲在3班,鲁生明在5班,陈红霞在6班。我们之间的关系不知不觉变淡了,再后来刘慧玲、鲁生明、常海萍陆续退学、毕业,回家务农,只有我和陈红霞一路考入了高中......再后来……总之,我们每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路,但是直到现在我们都无法评估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大概是年,我们五个人又意外地聚在了一起,回忆小学时光,我们当即决策,凑了一筐鸡蛋和两条烟,一起去二旗小学探望班主任封彦礼老师。那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从那以后就真的是天各一方,各奔东西了。尽管陈红霞和常海萍现今依旧保持着联系,但是总感觉彼此有那么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有些故事,我们以为到了结局,其实还没有演完。有些故事,我们以为还没有剧终,其实结局早就被暗示。年,小学六年级,小升初考试结束后,我和陈红霞、张丽萍,三个人突发奇想,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毕业纪念旅行。那天也很奇怪,好像全班找不着其他人人了,就剩我们三个人。我们各自骑了自行车,一路往西,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只记得我们从邻近的邵西村回民桥穿过唐徕渠,最后一直骑到西干渠大堤上。我们走错了道,西干渠上找不到过河的桥,我们过不去,对岸的神秘勾引着我们,我们束手无策。无奈之下,只好坐在西干渠堤坝的柳树下,三个人畅谈人生,遥想即将到来的初中生活,彼此很兴奋。那天天气很好,水面上刮着舒爽的清风,长渠流润,绿廊无垠。我们一起渡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彼时彼景,几十年后都记忆如初。在我一生中,再也不曾复制过那个美好的下午。但是,我们的小学六年生活终究还是结束了。条件所限,我们班级没有拍下集体照。现今除了五六个同学以外,其余的都失去了联系。年,我即将离开宁夏的那个夏天,暑期的某一天,午后突降一场大雨。我突然想去母校小学看看。时值放假,校园大门紧闭,空旷无人,我从大门翻了进去。教室门前的花圃刚刚遭遇暴雨冲击,东倒西歪,一片狼藉,红的、粉的、白的、紫的花瓣在空中零落。曲终人散,再也听不到当年的书生朗朗,再也看不到老师同学的当年模样。一个人徘徊许久,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大概是年左右,因为生源不足,二旗小学最终被并入了五道渠小学,也就是我上学前班的那所学校,办学长达十五年的二旗小学结束办学。造化弄人,继五道渠小学合并二旗小学后,没过多久,二旗村合并了五道渠村。人生总是充满各种变数,冥冥中又充满了各种巧合。往事回思如细雨,昔日重温似春潮。一转眼小学毕业快三十年了。随着年龄增长,感觉这个世界的浑浊和无望时,学生时代的记忆却越发变得清晰透亮起来。重温少年岁月,我们有过种种挫败和忧伤,也有过快乐和奔放。我们的自尊遇到过伤害,也受到过温情的抚慰。我们少不更事,却有一颗淳朴的心。我们早早地成熟,感受到生活的不易,品尝过现实中的很多的不公平,却在不知不觉中成就了强大、勇敢、坦荡的内心——这个世界终归是平的。回忆往事,本质上是在寻找那段时光中的自己。回望走过的心路,只是为了捡拾全新的能量,激发自己更好地前行!汤俊ing 惬听风吟·感悟人生
|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银川又多两个功能强悍免费健身的好去处
- 下一篇文章: 洪洞大槐树的移民真相大揭晓,迁移的